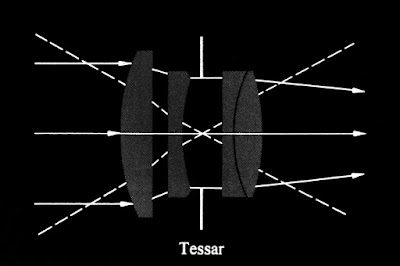想談一談重讀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感受﹝我看的是林少華翻譯的版本﹞:
一. 覺得永澤與渡邊談及外務省考試的對話相當精彩﹝65 至 67 頁﹞:
『「那你為什麼還要進外務省呢?」
「……不過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翻自己的拳腳。既然施展,就得到最廣大的天地裏去,那就是國家。我要嘗試一下在這臃腫龐大的官僚機構中,自己能爬到什麼地步,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懂嗎?」
「聽起來有點像做遊戲似的。」
「不錯,差不多就是一種遊戲。我並沒有什麼權力欲金錢欲,真的。……有的只是好奇心,只是想在那廣闊無邊而險象環生的世界裏一顯身手擺了。」
「也沒有什麼理想之類的東西嗎?」
「當然沒有!」他說,「人生中無需那種東西,需要的不是理想,而是行為規範!」
…… 「嗯,永澤君,你的所謂人生規範是怎麼一種貨色?」
「你呀,肯定發笑的!」
「我不笑!」
「就是當紳士。」
我固然沒笑,但險些從椅子上滾落下來:「所謂紳士,就是那個紳士?」
「是的,就是那個紳士。」他說。
「那麼當紳士,是怎麼回事?要是有定義,可否指教一二?」
「紳士就是:所做的,不是自己想做之事,而是自己應做之事。」
「在我見過的人當中,你是最特殊的。」我說。
「在我見過的人裏邊,你是最地道的。」他說,隨後一個人掏腰包付了賬。』
── 不單止內容風趣幽默,還很有電影的感覺,有如鏡頭反覆指向永澤與渡邊。
二. 對渡邊對初美的情感感到不解﹝251 至 252 頁﹞:
『……但初美這位女性身上卻有一種強烈打動人心的力量,而那絕非是足以撼倒對方的巨大力量。她所發出的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力,然而卻能引起對方心靈的共振。……我一直注視她,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這種感情震顫究竟是什麼東西,但直到最後也未能明了。
當我恍然領悟到其為何物的時候,已是十二三年以後的事了。……我猛然想起了初美,並且這時才領悟她給我帶來的心靈震顫究竟是什麼東西──它類似一種少年時代的憧憬,一種從來不曾實現而且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憧憬。這種直欲燃燒般的天真爛漫的憧憬,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遺忘在什麼地方了,甚至很長時間裏我連它曾在我心中存在過都記不起了,而初美所搖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長眠未醒的「我自身的一部分」。當我恍然大悟時,一時悲愴之極,幾欲涕零。……』
三. 對渡邊與玲子在阿美寮的一段對話﹝176 至 177 頁﹞:
『……「把病員和職員全部對換位置還差不多。」
…… 「我們的正常之處,」玲子說,「就在於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。」』
以及渡邊剛從阿美寮回東京後見到街上的光景﹝ 197 頁﹞:
『……面對如此光景,頭腦漸漸亂成一團,茫無頭緒。這到底算什麼呢?這紛亂雜陳的場面到底意味着什麼呢?』
── 感到相當妙。兩者皆指出「正常」與「不正常」的相對性,令人反思將思想或行為與眾不同的人歸類為「不正常」,將其標籤為「精神病人」,甚至禁錮他們的做法是否正確。似是在指出多數人盲目活在社會體制之下不懂反思,以及控訴社會對非主流思想的禁制與壓迫。
四. 就以下渡邊腦際中的話,產生了莫大的共鳴感:
「文章這種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納的,只能是不完整的記憶和不完整的意念。」﹝10 頁﹞
「或許我的心包有一層硬殼,能破殼而入的東西是極其有限的,所以我才不能對人一往情深。」﹝32 頁﹞
「我時不時向空間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,但指尖什麼也觸不到。」﹝34 頁﹞
以下這句,更是妙不可言:
「我只消嗅一下書香,撫摸一下書頁,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。」﹝35 頁﹞
日文原文:「その本の香りをかぎ、ページに手を触れているだけて、僕は幸せな気持ち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た。」